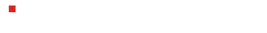频频发生,这不禁让人们发出疑问:为何城市总是难以逃脱被水淹的命运?深入探究极端气候与城市排水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试图揭开这一现象背后的神秘面纱。古特雷斯曾严肃指出,地球已然。君不见,六月的极端高温犹如烈火炙烤大地,七月的极端降雨又似天河决堤,曾经罕见的历史级暴雨,如今竟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日常景象。
每当我们翻阅新闻报道,瞧见城市于暴雨中沦为汪洋的景象,内心总会泛起强烈的疑团:城市怎会如此轻易被水淹?新建开发区更是积水 “重灾区”,这到底是为何?难道中国城市排水系统真如部分人所想那般不堪?实则我们需先认清一个客观状况:严格来讲,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下水道近乎于无。但这绝非否定中国排水体系,因排水系统种类多样,下水道只是其一。下水道可拆解为 “下水” 与 “道”。“下水”包含城市生活垃圾污水、工业污水、大气降水等各类汽水;“道” 即如巴黎、东京等城市的地下廊道式排水设施。
不妨以享有城市下水道楷模盛誉的巴黎为例,这样便能清晰地领悟到何为 “道”。在诸多经典电影场景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主角们在宽阔深邃的下水道中并肩奔逃的画面,这里所说的便是那种如同迷宫般庞大的排水廊道。它往往深埋于地面数十米之下,以其巨大的物理空间令人惊叹不已。例如,巴黎的下水道在地面50米以下,宽度超过5米;东京的下水道则更是深达地面60米以下。相比之下,我国所采用的并非这种廊道式排水系统,而是管网式排水,主要依赖各类污水管道。这些管网的口径大多在一米左右,并且掩埋在相对较浅的地下位置。
那么廊道式就一定优于管网式排水系统吗?不是。二者的选择像科技发展的岔路,选定后就会沿此发展。我国选管网式排水系统是有原因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原有排水系统年久失修,不足以满足城市发展对现代化排水设施的需求,北京、广州、沈阳等城市在苏联帮助下复制了苏联的地下管网式排水系统。它的优势是经济、建设快,能快速搭建排水框架,但后来弊端渐显,主要是对本土环境适应性差。
苏联大城市降水少,如莫斯科年平均降水量仅582毫米,中国与之不同,秦岭~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上,广州达1600毫米。近年来,郑州和北京部分地区单次降雨量可达700毫米。中国的管网式排水系统在城市小、发展慢时还能运转,随着城市扩张和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短板显现,无法适应城市规模扩大和降雨变化。河海大学一篇论文剖析了我国排水管网建设问题,除规划和维护不足外,还指出雨水设施水量复核标准这一关键指标。
2021年《室外排水设计标准》规定了排水设计重现期,如3~5年重现期表示能应对3~5年一遇的暴雨强度。我国大城市~特大城市中心城区排水设计标准多针对2~5年一遇降雨,非中心城区和中小城区是2~3年一遇,超大城市中心城区重要区域按5~10年一遇设计。但郑州和北京等地遭遇的是百年一遇甚至更罕见的暴雨,现行标准已不足以满足实际需求。
需澄清,并非否定管网式排水系统。国家城市积水排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工程师称,从排水设施性能看,管网式与廊道式相比并不差,设计合理、调度精准,二者都能出色排水。他强调的是排水系统维护、扩建及磨合的重要性。中国管网式排水系统发展历史的磨合时间短,仅六七十年,巴黎建下水道系统却用了126年。可见时间对排水系统发展完善至关重要。中国式排水要坚定沿自身道路前行,且已迈出坚实步伐。
依据国家统计局近两年所公布的数据,从排水管道长度以及污水处理能力这两项关键指标来考量,广东省在全国范围内表现得格外突出,其城市排水管道长度远远超出其他城市,污水处理能力更是处于断层式领头羊。此外江苏、山东以及浙江等省份在这方面的表现也颇为出色。颇为巧合的是,这些在管网设计与调度方面表现卓越的地区,恰好均位列我国GDP 排名前列的省份。综合气候、面积、规划数据等因素,前述数据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南方降雨多,城市排水建设投入大,属地理差异常规应对。若相关地区朋友分享排水体验,可为精准参考。
谈完管网式排水,再看青岛下水道。青岛德国下水道被传为美谈,其他城市遇极端降雨时,有人夸其防涝作用,虽有可赞之处,但不可夸大。德国在青岛建80公里排水管道,现仅约3公里在使用,占比千分之一。青岛少内涝,一是自然植被覆盖率好,截留雨水减流速、缓排水压力;二是地势西高东低且三面临海,积水易排入海,地形优势使然。此外,青岛及中国城市建设发展中的努力也重要。2016年,青岛入选国家第二批综合管廊与海绵城市试点且是唯一双试点城市,相关建设明显提升其排水效果。
总而言之,在当今全球面临气候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重新审视和反思自身的排水系统,深刻认识到一成不变必将陷入困境,消极应对更是毫无出路。即便是在下水道建设方面颇具声誉的德国和法国,在极端天气的肆虐下,其城市也难以避免遭受水淹的命运。例如今年7月北京所遭遇的极端强降雨,据官方报道,局部区域所记录到的降雨量堪称140年一遇,面对如此罕见的暴雨强度,世界上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排水系统能够完全抵御。这无疑是整个人类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艰难困境。
近年针对城市内涝与气候应对有综合方案——海绵城市,是城市耐水长远之策。其理念是构建河湖、池塘等水系与植被、草沟等构成的多元ECO,吸纳、储存、净化雨水并按需利用。中国2012年起开展水弹性城市建设试点,计划2030年让城市建成80%以上达建设目标。国外有类似举措,如日本雨水滞留渗透计划、英国水敏感性城市设计,皆为让城市具更强水弹性应对气候。
通俗理解,水弹性城市似与水和谐共生的太极智慧,以柔克刚,分流缓冲暴雨冲击。它是中国古老智慧于现代城市建设的回归创新。如故宫,建筑走势顺应北京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北高南低、中间高两边低且有坡度利于自然排水;其水系规划更精妙,内有内金水河,外有护城河,宫殿院落排水系统由干线支线交织,明沟暗渠等多样设施构成庞大有序网络,大小水系协同运作契合海绵城市概念。降雨时,故宫雨水经沟渠汇干线入内金水河再流护城河,使其在三大殿植被少处也无积水,600年过去,如今面对严峻气候挑战仍排水卓越。
在南方地区,还有一个更为系统且覆盖面积更为广阔的古代排水工程典范——江西赣州福寿沟。这是一套罕见的古代地下排水沟与周边坑塘水系紧密结合的排水系统,始建于北宋熙宁年间,由当时的赣州知州刘彝亲自主持建造。根据清同治年间绘制的福寿二沟图以及1990年代重新绘制的福寿沟路线图进行测算,早期的福寿沟总长度不少于12.6公里,沟体截面积普遍约在0.8 - 1平方米之间,在古代而言,这无疑是一项规模宏大、意义非凡的市政级别排水管沟工程。
福寿沟非独立运行。华南理工大学吴庆洲教授报告深入探讨,它依地形与周边池塘连通,经单向水窗连城墙外城壕与河流,构建单向排涝蓄洪体系,如海绵吸纳、存蓄与排放雨水。历代有维护修缮,1963年大修,2019年成文物保护单位,现仍部分完好,在赣州排涝中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因城市规模扩张,面对极端降雨难以独担保障重任。
排水系统变革发展外,要知海绵城市虽先进完善,对极端暴雨承载有限。其意义一在提高雨水吸纳存蓄力,减中小降雨时排水压力;二在助水资源合理规划利用与生态维护,利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弹性城市侧重长期规划与日常应对,属渐进提升水弹性阶段,极端降雨超常规设计标准,会使海绵城市排水功能遇挑战甚至致城市排水系统瘫痪。
以海绵城市试点城市郑州为例,在《郑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文件中,对于水安全的规划标准有着明确的规定。当细化至城区各个组团做多元化的分析时,我们会发现其设计降雨量普遍不超过30毫米。通过这一些数据,我们大致能了解水弹性城市在应对降雨时的承载能力上限。当降雨强度达到千年一遇的罕见程度时,海绵城市的排水功能也会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有效应对。在极端降雨这一现实难题面前,有关专业人士曾明确指出,海绵城市的基本功能在于解决中小降雨过程中的径流蓄滞问题,而对于突发的特大暴雨,其已经超出了水弹性城市的设计应对范畴。
郑州水弹性城市建设努力未白费。郑州市城建局称,截至2021年5月,已累计消除77%易涝点,成果渐显。海绵城市有用且需发展完善,因很多城区连中小降雨应对设施都不完备,多为“水泥城市”,晴天热岛效应,雨天内涝。郑州经验启示,海绵城市建设之上需引入如城市深隧排水系统等强大设施。深隧即城市深隧排水系统,国外有实践经验,由主隧道、竖井、排水泵组、通风设施、排泥设施组成,各部分协同,如地下巨龙在强降雨时保障城市排水正常运转。
深隧排水系统作用多大?看实例便知。伦敦泰晤士河深隧建成后,可使溢流次数从每年60次减至4次,缓解排水压力,改善水环境。日本江户川排水深隧1992年始建,最大排洪流量每秒200立方米,应对暴雨关键。上海深隧建设有进展,可将苏州河沿线排水能力从一年一遇提至5年一遇,能应对百年一遇降雨,保障区域不瘫痪,路中积水不超15厘米,还能基本消除初期雨水污染,特定降雨量时泵站不溢流。
气候危机下,有深隧的城市更稳定。我国除上海外,武汉、广州、深圳有多条深隧在建,北京、成都处于规划阶段,北京深隧若成熟,永定河压力能减小。今年3月,中铁十八局联合体中标杭州相关项目,是我国排涝规模、动静、埋深最大的深隧工程,建成后保护范围可达213平方公里,对改善水环境、防内涝作用重大。深隧对实施工程技术要求高,但我国隧道技术发展快、积累多,有关技术可应用转换。虽深隧建设费钱,却是极端天气下减民生损失的可靠办法。深隧与海绵城市搭配是城市排水长远出路,较为可行,关键是与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赛跑。